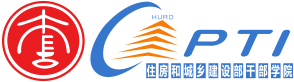

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IUS)副院长,IUS城乡文化开发与营销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说到“城市病”,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大城市才有的问题。很少人会想到小城市也有“城市病”,而且还呈现出小城市特有的特点,甚至有些小城市病得比大城市还重。
若放任“小城市病”持续蔓延和发酵,将使得小城市难以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和区域,并最终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更加深陷于“大城市病”之中。
当前,以交通拥堵、人口膨胀、人才过剩、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为特征的“大城市病”已广为人知,而日益严重的“小城市病”却较少有人注意。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小城市病”应引起现阶段的更多关注与警惕。
什么是“小城市病”
“小城市病”主要指城区常住人口少于50万规模的城市出现的人口流失、产业衰退、资源枯竭、就业艰难、生活方式庸俗化、创新人才缺失、缺乏文化活力、发展动力欠缺等诸多城市问题。
这些小城市的问题集中体现为一种“庸堕化”现象,即精神生活庸俗化、经济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小城市病”的长期存在,将直接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有超过1800个城区人口少于50万的小城市,其中许多小城市都或多或少形成了“小城市病”。最近在房地产领域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多卖一套房,三线城市就增加3套库存房”的业内警告,从一个维度说明了小城市的人口及资源外流还在持续加剧的危机。
中国“小城市病”在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中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发展后果:
一是“滞后型城镇化”带来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旦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人口拥挤、治安恶化等城市病,这种小城市病主要体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净流入较多较快的小城市。
二是“超前城镇化”带来的供给过剩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包括小城市在内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开展了“摊大饼”似的城市扩张,开发区、新社区迅速崛起,工业厂房与居住楼房呈现大面积过剩,烂尾项目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小城市的空城化与市容萧条的局面。
由于大多数小城市受人口、资源和社会文化惯习的影响,城镇化发展的能力越来越弱化,与大城市产生更大的鸿沟,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其经济结构能够有实质性改善的动力与机会。特别在经济下行周期,在大城市持续“抽血”小城市资源的极化发展格局之下,诸如产业结构单一与就业机会不足、人才持续流失、住房供给过剩与资产价格走低等各种发展性矛盾不断积累,弊端不断放大,我国各地区的小城市病还将会持续爆发。
“小城市病”的症结所在
文化上,小城市生活方式存在的“庸俗化”的倾向。中国的很多小城市都缺乏象征文化品位与时尚文化氛围的空间设施,究其原因,从商业角度讲,是没有文化消费群体,从城市文化角度理解,则是缺失文化生活的氛围和土壤。这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最终拉低了小城市的文化层次和品位。
在缺失文化格调的小城市,市民的精神生活样态较之大都市显得较为单调,麻将、扑克、电视剧占据了主流,赌博风气日渐浓厚,许多公务员、青少年、赋闲人员以及拆迁上楼的农民都普遍爱好打麻将等诸多恶习。小城市普遍流行的庸俗生活方式逐渐弱化了城市文化活力,又阻滞了新质文化生活方式的生成。
经济上,小城市因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活力日趋弱化。大多数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其城市形成之初大多依赖少数大型工业企业或厂矿型企业起步,农业人口就地转化为工人占比较高,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少数几个企业或行业就业。由于资源型行业受国内外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小城市的经济往往容易陷入周期性的低迷期,从而导致城市静态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区间。全国有130多个资源枯竭性小城市,因为产业资源的衰退,不少小城市陷入了“枯城”化命运.。
同时,结构单一与经济衰退的小城市,就业门类较少,就业机会紧张,导致了人口外流明显的现象。另外,小城市因产业结构单一,活力不足,任何发财的资源和机会都显得稀缺,导致城市资源争夺呈现暴力化倾向。在不少小城市,因为争夺各类土石方、土建和建筑工程和矿山、林地、鱼塘承包等问题而发生过各种形态的暴力冲突。这种暴力手段获取项目的现象长期存在,使得一些老实本分人根本无法获得发展机遇,创新创业也很难在小城市开展。
社会结构上,小城市社会生活的“强关系化”导致选择机会不足。小城市因人口规模小,人口结构相对本地化为主,职业多样性和人口异质性较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太小,因而高度重叠,无法形成大都市精神,从而导致熟人化社会特征非常明显。熟人社会在小城市的社会交往中容易形成一种“强关系化”趋势。
这种“小城小圈子”的垄断就是一种“强关系化”的结果。小城市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非常有限,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人们为了谋得一份工作、一个挣钱的机会、方便办事或就医、就学,都会在第一时间寻求各种关系。强关系社会导致了小城市生活的逼仄性,最终使得小城市开放度低、社会网络规模小,个体选择机会及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大大降低。
“小城市病”对人才和资源的影响
小城市出现了创新人才的荒漠化趋势。在新一轮城市竞争时期,小城市的庸碌化逐渐被固化,对于高素质人才而言越来越丧失吸引力。极化发展的“北上广深”等大都市与小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地域反差。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简单的物理空间与产业结构层面,更多地体现为城市性格、城市活力、城市能级、发展机会、城市自由度、人口多元化等层面。
小城市在人口的同质化、熟人化、规模小、密度低的格局之下,又通过“循环因果累积效应”而逐渐庸堕化,最终无法吸引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无力汇聚创新型人才。青年人才过度的单向流动,导致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低层次化。失去青年创新群体的支撑的小城市,有可能陷入创新人才荒漠化和创新文化枯竭的困境。
中国城市发展的极化现象,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对小城市的各种资源典型的“虹吸效应”。创新人才与知识经济全部集中在高校密集的大城市,小城市缺乏高等教育资源,难以形成知识生产的人才、机构、机制,更难以培育出创新文化氛围。
大学毕业生和高级白领所青睐的研发机构、金融机构、外企、国企总部、行政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也几乎都分布在一线城市及省会大城市。这些吸引青年人才的机构,在中国的小城市几乎空白。
具有文化品位和知识审美层次的创意阶层与文艺青年群体,随同优质教育及就业资源的结构性缺失,最终加剧了小城市对精英群体的“市场化排斥”。因此。这种因小城市局限性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趋封闭、活力缺失,最终导致小城市固化了自身的庸俗化、封闭化的社会结构。
“小城市病”有何危害
若放任“小城市病”持续蔓延和发酵,将很有可能形成一种“小城市发展陷阱”。短期内,中央推动的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在小城市已经举步维艰。由于大城市的人口持续集聚效应,一线城市房价持续走高,追涨心理十分明显,购房资金和人口继续追涨一线、二线特大城市。小城市很有可能持续被“虹吸”、被逃离、甚至被抛弃。
同时,由于小城市过去十多年所开展的城市化建设开发与投入,地方债务已经累积超过警戒线,在去库存乏力、经济活力不足的形势下,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而这种困难又将延缓或阻滞小城市的发展动能,最终陷入互为因果、前后矛盾的两难境地。
长期来看,“小城市病”将使得小城市难以形成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和区域,最终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更加深陷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化的“大城市病”之中。因此,“小城市病”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与反思。
“小城市病”该怎么治
总体上来看,一些陈旧的发展观念应该摈弃,比如盲目地招商引资,盲目地在城建项目中大干快上,盲目地在发展中贪大求全。
首先,城市发展渠道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才引智。从向大企业招商到向大学招才,这是修复小城市人才构成的一个选项。比如,江苏靖江市引入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建成江苏长江北岸的第一家县级大学,8000多名师生为当地带来化工、金属材料、机械制造等专业的人才,与当地产业特色高度契合。更直观的效果是学校还没开学,周边的小商铺、餐厅甚至咖啡馆都已经聚集起来,使当地服务业蓬勃发展。
再者,城市发展方式从扩大增量转变为优化存量。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特色将是未来每一个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特色的城市就没有竞争力。而特色需要从城市既有的存量上去挖掘,去找到城市有竞争力的一面。做好这些工作,是要为发展“止损”,通过治标为“小城市病”的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
此外,城市发展取向从搬迁移植转变为交流合作。以往小城市都希望把大城市的项目和资源直接移植到本地,但许多并不成功。如果采取交流合作的方式对接城市产学研的高端资源,不强求生产中心、研发中心、人才基地落户,而更加看重交流合作带来的带动效应,或许能减少搬迁移植的风险。比如,有些小城市就通过对接高端科研院所,在本地设立研究机构,实现研发人员的交流往来,带动小城市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相关人员的思维生活方式、文化需求的转变。
要根治“小城市病”并非朝夕之功。希望国家能够把部分产学研的节点和终端放在小城市,通过与大城市的频繁互动和交流,带动小城市合理分工布局。应当考虑出台政策,鼓励小城市本地资源的优化升级,嫁接外部资源,以我为主对外合作而不是单纯招商引资。通过互利双赢的合作带来小城市产业、人文环境的量变,假以时日再寻求发展上的质变。这恐怕是小城市必须正视的一条发展道路。